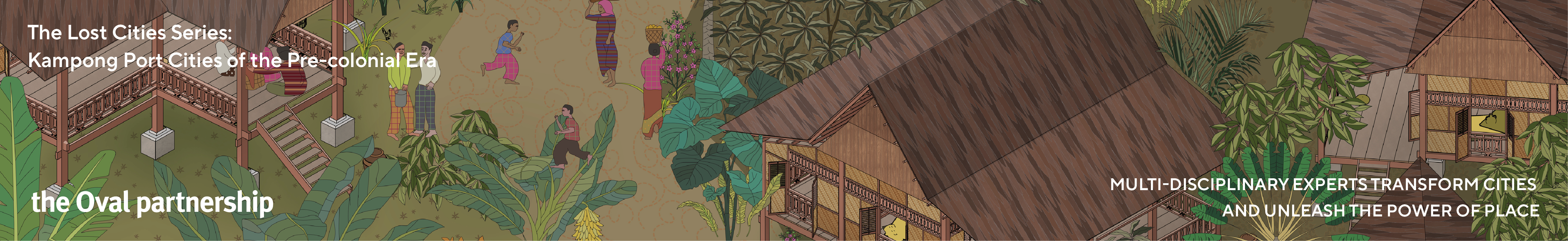香港新地标The Henderson 流动如水的城市光影
新商厦设计由Zaha Hadid Architects操刀,不但与城市融为一体,同时挑战摩天大厦的固有建筑概念
六年前,恒基兆业地产斥资233亿港元(折合约30亿美元)投得美利道2号,该址原为多层停车场。价格惊为天人,当时更曾创下全球最高价值地皮的纪录。根据项目发展限制,新建建筑物的高度不得超过190米,即与香港大部分屋苑相若,亦不及全港最高两幢摩天大厦 ── 国际金融中心及环球贸易广场 ── 的一半高度。
但以地段而言,该址实在所向披靡。美利道2号位于遮打花园东侧边缘,位处香港商业及司法权力核心地带,繁华景象尽收眼底,另毗邻终审法院、历史悠久的中国银行大厦、大会堂、香港会所、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,以及由Norman Foster操刀的汇丰总行大厦。因此,作为香港市值第三大的发展商,恒基地产自然希望兴建全城甚至举世瞩目的大厦,在林立建筑地标的香港脱颖而出。
为此,恒基地产委聘Zaha Hadid Architects(ZHA)负责设计工作。该建筑事务所由已故的伊拉克裔英国建筑师Zaha Hadid创办,她善于采用数码参数设计,笔下建筑流动如水,流线如叶。 Zaha早于1983年为香港人所认识,当年为香港山顶私人会所构思方案,设计犹如与周边景观融为一体,但直到2013 年,她于香港的首座作品才正式面世,那便是香港理工大学的创新楼,而美利道2号The Henderson则是ZHA迄今为止在香港最大规模、最具野心的项目。

左图:The Henderson(电脑模拟效果:MIR;相片来源: Zaha Hadid Architects)
右图:从遮打花园望向The Henderson。(电脑模拟效果:MIR;相片来源: Zaha Hadid Architects)
为监督项目进展,ZHA总监Sara Klomps于五年前移居香港,她表示:"此建筑项目要非同凡响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" 不但在视觉层面如是,从功能角度来看亦如是,使用时下设计用语来说即是 "面向未来",但更精准的术语或许是灵活应对未来。她续道:"我们的目标是兴建一幢能够满足未来需要的商厦。虽然我们着手工作时尚未爆发疫情,但当时已从可灵活应变的建筑设计作切入点。"
从一开始,设计便定下楼底为3.5米高,即每层可以容纳一个交易大堂,属商业地产市场相当少见。因此,商厦仅得36层,相比同等高度的住宅大厦则近60层。有赖六条巨型支柱和一个侧面核心结构,每层都采用无柱设计,将核心元素如电梯、楼梯和管道移至旁边,而非置于中心位置,从而令空间更寛敞开扬。 Klomps说:"此举再次说明,设计要将灵活性考虑在内。" 她指出,不少公司正在物色面积更大兼无阻隔的协作工作空间。 The Henderson的每层面积稍稍大于43,000平方米。
设计过程期间,新冠疫情来袭并持续数年,回想着手设计项目之时,便将适应力考虑在内,实在具先见之明。 Klomps说:"当时,充足的通风、采光、空间等其他因素变得相当重要,可幸室内设计并未全面完成。我们设计了免触式通道系统,让用户由大厦入口走到座位的过程中,无需接触任何公共设施。" 高楼底有助空气流通,再加上额外的空气过滤作辅助。此外,当室外空气质素良好时,通风系统便会自动启动。

The Henderson位处香港的权力核心地带,同时将遮打花园及闹市繁华景象尽收眼底。(电脑模拟效果:MIR;相片来源: Zaha Hadid Architects)
大厦亦设有户外空间,主要位于楼高两层的防火层,让员工有机会出外呼吸新鲜空气。 Klomps表示:"空间绿意盎然,环境开扬,供租户稍作休息或享用午餐。"
商厦不仅为租户提供户外空间,亦设有若干公共空间。 Klomps指出,这些空间将定义公众如何与建筑物互动。该址的土地契约要求将其纳入中环的行人天桥网络。 「这种做法在香港很常见,我们必须做到互联互通。有不少建筑物的设计是让路人途经商场,我们本来也可以这么做,但却更希望让路人一直置身市区环境。我们想保持与公园的连系,而这与汇丰总行大厦的构思非常相似。」她指的是附近位处公共广场之上的的汇丰总行。"犹如将整座建筑升起,营造流通的公共空间。"
The Henderson的地面层和行人天桥层将会是园林公园,餐厅食肆林立其中。 Klomps说:"位处如此重地,我们不希望像其他建筑物一样,将地面层也作商厦用途,截断公园及公共空间,纯粹设有一个小小的大堂便告完成。" 此举表示恒基地产需要作出牺牲,皆因公共空间会占用建筑物的总楼面面积,即减少发展商可以出租图利的空间。"恒基地产积极踏前一步。这设计用上不少总楼面面积,但他们很乐意放弃这些空间,以提供不一样的元素。我们并不常遇到愿意拨出这些空间的客户。"
Klomps表示,在提供绿化空间或环保设施相关的总楼面面积宽免方面,香港异常吝啬,而有如此评价的不只她一人。去年,当我们访问建筑师兼发展商蔡宏兴时,他亦慨叹香港设有很多建筑限制,如新加坡和深圳等亚太地区城市便会提供相当具吸引力的激励措施,以鼓励发展商构建如The Henderson的公共空间及绿化环境。他说:"香港的法规还未跟上步伐。我们的法规已不合时宜,有碍此类设施的发展。"
总楼面面积限制亦会局限可持续的建筑设计。 Klomps说,在大多数其他城市,如The Henderson的大厦均会采用双层中空幕墙,当中形成空气气垫,有助调节建筑物室内温度,避免过度降温或加热。但香港是寸金尺土之地,尤其是单单投地便需花费数以亿计的金额。 Klomps 表示,"总楼面面积宽免包含一个 250 毫米的幕墙区域",可见斟酌空间相当有限。根据香港的总楼面面积相关法规,即使在每层安装百叶窗来遮挡阳光,亦不得向外伸出超过300毫米,否则需要削减建筑物其他地方的总楼面面积来填补。大多数发展商都不愿意作出这样的牺牲。 Klomps说:"在香港,每一幢 [新]建筑的外观都是平平滑滑,实在非常可惜。"

左图:The Henderson地面入口及大堂(电脑模拟效果:PixelFlakes;相片来源: Zaha Hadid Architects)
右图:The Henderson的弧形玻璃幕墙(电脑模拟效果:Cosmoscube;相片来源: Zaha Hadid Architects)
在种种限制下,要令建筑尽可能符合环保原则,巧思必不可少。在符合建筑规定的许可下,大厦使用反射率最高的玻璃,内部采用银涂层遮挡阳光,并采用具有高遮阳系数的高性能玻璃。 Klomps说:"我们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来减少日光吸收。" 此外,楼顶装有太阳能电池板,控制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"太阳能幕墙降温装置",当最烈日当空时,装置会送风到玻璃幕墙内部位置。
虽则这是大厦的一大特色,但大多数在当中工作或路过的人永远都不会注意到。建筑物要成为地标,便是在于其外观。洋紫荆是香港的市花及城市象征,而设计正正以洋紫荆含苞待放的形态作为灵感,其起伏之美与周边方正典型的大厦形成鲜明对比。 Klomps表示,结构的优美曲线是设计主轴,让城市宛如穿梭建筑并在周边一带流动。对于流动形态(ZHA作品的特色)纯粹是为了美观的说法,她很快便作出辩解。
她说:"这从来都不是纯粹在形式上。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将灵活性连系到方形盒子? 任何人凭第一直觉,都会认为盒形比圆形建筑物更为实用,而我并不太苟同。如果你观察大自然的有机形态,你会发现不存在盒子 ── 好吧,应说是几乎没有。如果设计不是单循直线发展,不在既定框框之内,我们便能让人们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使用建筑空间。"
她续道,曲线具有情感效用。"当出现惊喜或予人柔和感觉时,便会令人对建筑产生不同的认知和认同。正因如此,像[Friedensreich] Hundertwasser和[Antoni] Gaudí等建筑师能引起莫大共鸣。我们设计每一个项目时,都会让空间相互流动,并创造某种中间地带。某程度上,这些建筑因此能够成为城市及当中居民的一部分。"
The Henderson即将竣工,明年初对外开放。虽然无法确定发展商的花费是否物有所值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:单凭其与众不同之处,The Henderson已成为立心要打造的地标。
作者:Christopher DeWolf
本专栏为 bodw+ 与 Zolima CityMag联同呈献。Zolima CityMag是香港网上文艺杂志,以深入角度探讨本地艺术丶设计丶历史及文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