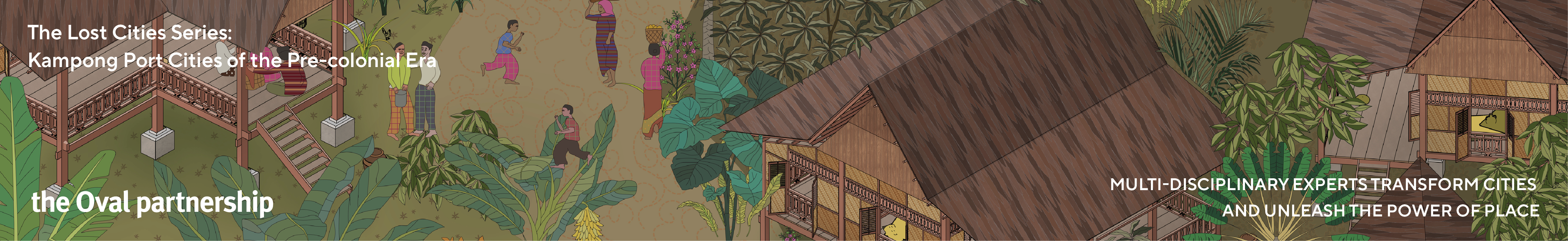理想家園:設計更美好的公營房屋
建築師們正想方設法改善社會房屋,而香港就有不少例子可供借鑑
環顧世界各地,馬岩松及其創辦的MAD建築事務所已設計了不下數十座惹人注目的建築,包括形如旋動流沙的哈爾濱大劇院、位處內蒙古沙漠、深受地質環境啟發且呈青銅色的鄂爾多斯博物館,還有多倫多郊區的Absolute World雙子公寓,其婀娜多姿的曲線造型讓它同時被暱稱為「瑪麗蓮夢露大廈」。
MAD的最新項目以不一樣的方式引起關注,因主角是公營房屋。百子灣公租房於2021年竣工,鄰近北京商業中心佔地43公頃,內有花園、商店,以及合共提供4,000個單位的12棟公寓。無論是中國的公營房屋或私人樓宇,往往採用千篇一律的倒模設計,馬岩松及其團隊為打破這個常規,在世界各地進行長達八年的公營房屋調查研究後,才著手設計百子灣公租房。

左圖:Le Corbusier設計的馬賽Cité Radieuse(攝影:Giulia Duepuntozero,相片來源: Wikimedia)
右圖:Le Corbusier設計的馬賽Cité Radieuse室內小街(攝影:Michel-Georges Bernord,相片來源:Wikimedia)
當然,馬岩松並非第一個關注社會房屋的世界知名建築師。 1952年,瑞士建築師Le Corbusier設計了馬賽公寓Unité d'habitation,從此改變高樓大廈的性質。這是一幢興建在架空式樑柱上的混凝土大廈,將住宅、商店和社區設施匯聚於同一屋簷下。後來,世界各地都仿效這種手法,務求改善城市的住屋條件。馬賽的La Cité Radieuse 便是一個著名例子,建築設計建基於Le Corbusier「模組化」系統的人體工學原則,旨在令空間比例更為舒適;加泰隆尼亞建築師Ricardo Bofill視社會房屋為展現後現代主義建築活力的平台;位於巴黎附近由他設計的宏偉公共屋邨 Les Espaces d'Abraxas,正好證明可負擔房屋亦可散發如皇宮般的魅力。
遺憾的是這些設計雖然如此創新,其中許多旨在取代都市貧民窟的傑作,最終卻與貧民窟面對相同的問題。(其他如法國馬賽的La Cité Radieuse或英國錫菲的Parkhill,因其非凡建築而備受追捧並走向高檔化。) 雖然 Les Espaces d'Abraxas 仍然令人歎爲觀止,現在卻因成為販毒溫床而臭名遠播。當中最聲名狼藉的,也許是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的Pruitt-Igoe,屋邨由後來負責設計世貿中心的建築師山崎實操刀,即使擁有很高的知名度,但由於欠缺保養維修及公共安全,所以導致大多數居民最終選擇遷離。該屋邨於1955年竣工,不到20年便遭清拆。

左圖:鄰近巴黎的 Les Espaces d'Abraxa (攝影:Nell's Journey,相片來源:Flickr)
右圖:鄰近巴黎的 Les Espaces d'Abraxa (攝影: Fred Romero,相片來源:Flickr)
在全球不少地方,類似的個案令公營房屋背負污名。惟社會對公營房屋的需求有增無減。無論是美國德州農村地區,抑或是南轅北轍的荷蘭阿姆斯特丹市中心,世界各地都陷入迫在眉睫的住屋危機。隨著住屋成本飆升,加拿大和美國各大城市 湧現一個又一個的帳篷城市。至於香港,超過20 萬人居住在狹小的劏房,當中有家庭擠在一個只有50平方呎的空間,而露宿者人數在過去10年間上升近三倍,自疫情爆發起計則上升22%。
這些數字凸顯社會對公營房屋的需求十分殷切,目前在香港申請公屋,平均輪候時間為5.3年。但從世界其他城市的經驗可見,重要的是提供優質的公營房屋,並非單單是簡陋的容身之所,而馬岩松設計百子灣公租房便是出於打造理想家園的初心。去年,他在建築與設計網站 Dezeen的網上直播中分享:「我參觀了北京一些社會房屋(屋邨),建築採用封閉式設計,讓人感覺猶如置身監獄。不管外表有多麼美,居民都會感到孤立。」他決定採取相反的做法:百子灣公租房將城市引入屋邨,因此讓人感覺像是街區,而非四周築有圍牆的樓群。

左圖:百子灣街景(攝影:田芳芳)
中圖:百子灣街景(攝影:CreatAR)
右圖:零售空間融入百子灣(攝影:朱雨蒙)
多年來,香港已累積不少經驗。1953年,石硤尾寮屋區發生大火,為安置無處容身的家庭,首批徙置屋邨應運而生,住屋格局自此便出現不少變化。這些早期屋邨原本作緊急收容所之用,但從1960年代開始,政府開始興建永久性公營房屋,旨在將屋邨發展成完整的社區。由於空間所限,屋邨通常建於城市的邊緣位置,例如於1964年落成的彩虹邨,設計出自香港享負盛名的建築設計公司巴馬丹拿集團之手。
園境師兼香港大學講師Natalia Echeverri說:「這些公共屋邨面積龐大,可容納四至五萬人。如果你想把這麼多人遷移至一個偏僻的地方,那地方便必須包含一切生活所需。1960及1970年代,新建屋邨一般包括商店、街市、學校、診所,以及一個方便居民往來其他地區的巴士總站。
前香港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、現於沙迦美國大學任教的Jason Carlow說:「這是一種自治的城市主義 ──它們本身就是城市。香港人口密集的屋邨項目之所以成功,原因之一是與交通交匯處的良好連接。很多城市都沒有做到這一點,像紐約這樣的地方可能也有類似的密集式住宅大樓項目,但並未能與公共交通設施便利連接。」
私人住宅項目盡可能增加發展密度,務求為業主及發展商帶來更多利潤 ──所謂的「怪獸大廈」浮現眼前。可屋邨剛好相反,當中設有大量公共空間。設計師鄭惠冲說:「香港公屋成功創造了人們可以相聚並形成社群的空間。」他最近與攝影師 Kris Provoost合作記錄香港公共屋邨內的公共空間,作品目前於威尼斯建築雙年展香港展區展出。

左圖:Kris Provoost及鄭惠冲在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展出的裝置作品
中圖:香港穗禾苑(攝影:Kris Provoost)
右圖:鄭惠冲及Kris Provoost的香港屋邨繪圖
原因之一是公營房屋設計不斷完善。香港已經興建大量公營房屋,腳步亦未停下來,因而得以持續改進。香港超過一半的人口(即約360萬人)居於某種類型的公營房屋,包括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公共租住房屋,以及為中產家庭購買的大幅資助房屋。目前,香港共有130萬個公營房屋單位,並計劃在未來十年內再興建316,000 個單位,其中許多位於靠近深圳邊境的北部都會區等新發展區。
這將是探討公營房屋如何進行創新的良機。多年來,香港房屋委員會負責香港大部分公營房屋的相關工作,並逐步調整規劃和興建新屋邨的方法。雖然於2000年之前興建的屋邨,均採用房委會所謂的「標準大廈設計」進行規劃,但由於缺乏易於開發的用地,房委會不得不於地形更複雜的地方,改用因地制宜構件式單位設計。與此同時,單位本身也轉向制式化。曾經是由建築工人在現場人手建造的單位,現在則採用構件式,意即於其他地方預製組件,然後運送到建築地盤並進行組裝。
在今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中,設計及工程公司奧雅納為香港展區展示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方法相關展品,該公司代表何偉明博士表示:「目前,在香港的公營房屋項目中,近80%至90%的組件在工廠統一大量生產。」他指出,要製造一套配有浴室和其他內置設施的構件式單位,只需要一個月的時間,而且可以與建築物地基的施工同時完成。與傳統建築相比,這種方法更快捷、更便宜、更安全,同時可減少浪費及污染。這種建築方法特別為如新屋苑等超大型項目帶來裨益,尤其是公共項目,皆因所節省的資金可用於發展將來的公營房屋。

左圖:百子灣公共空間(攝影:CreatAR;相片提供:MAD 建築事務所)
中圖:MAD設計百子灣時,採用多種建築比例,營造多元化的氛圍(攝影:CreatAR)
右圖: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的百子灣(相片提供:MAD 建築事務所)
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法的效率雖高,但不無缺點,其中之一是尺寸:單位寬度通常需要少於3.5米,才能使用貨車運送組件到施工現場。另一點是缺乏靈活性。何偉明博士指出:「當生產組件後,設計就不能輕易改變。 」Carlow表示,狹小的空間和有限的間隔是香港公營和私營住宅建設的最大缺點。他說:「香港的做法有點僵化。我在想什麼樣的住屋模式可以讓家庭更靈活作出改變,增加家庭成員時可方便作出調整,並迎合不同的生活方式,例如在家工作。」
話雖如此,房委會在改善公共屋邨生活方面已下了不少工夫。十多年前,房委會推出一項綠化計劃,投放資源為屋邨居民興建綠化屋頂、綠化牆壁和社區花園。 Carlow說:「房委會一直非常積極作出不同嘗試。預製房屋有助降低成本,但他們也在思考更大的問題,例如城市熱島效應、城市規劃下的空氣流通情況及社區參與。與其他地方相比,房委會已推出很多相對進取的政策。」
房委會甚至為屋邨注入一些奇思妙想,例如以懷舊冰室作為藍本的牛頭角邨休憩處,以及描繪在街上看到飛機降落舊機場的啟德啟晴邨天花壁畫。

左圖:百子灣鳥瞰圖(攝影:Arch fast )
右圖:百子灣總體規劃(相片提供:MAD 建築事務所)
雖然馬岩松從未直接表示從香港屋邨汲取設計百子灣公租房的靈感,但其影響處處可見。與大多數香港屋邨一樣,百子灣公租房四通八達,設有住宅、商店及社區設施,四周環境綠樹林蔭。香港或許也可學習馬岩松的做法:馬岩松堅持增設文化場所,儘管政府並沒有相關要求;他亦調整每幢建築的高度和規模,以營造一種不拘一格的氛圍,但又不會過於雜亂;而大多數香港屋邨大廈的高度往往是一致的。
夢寐以求的屋邨新設計模式由此而生,適用於中國及至世界各地。馬岩松表示:「雖然只是稍作改變,但已經是對現狀的一大挑戰。」
作者: Christopher DeWolf
本專欄為 bodw+ 與 Zolima CityMag聯同呈獻。Zolima CityMag是香港網上文藝雜誌,以深入角度探討本地藝術、設計、歷史及文化。